

11月27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秒钟》在院线上映,这一档期比原定档期晚了近两年。上映四天,影片累计票房7000多万。对于张艺谋来说,这一票房成绩不算惊喜,但是在许多第五代导演新作失势之时,《一秒钟》的口碑倒是不错,保持了张艺谋在影迷心中的水准。

《一秒钟》电影剧照。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大时代中个体的遭遇。一个因为打架在劳改所很多年,不被女儿理解的父亲,听闻电影片头新闻简报里有自己女儿的影像,于是偷偷从被看押的地方跑出来。在他去追逐电影放映场次过程中与刘闺女、范电影等人物相遇,产生了一些交集。
电影中最动人的部分来自主人公张九声对女儿的爱,由这种深沉的父女情推动,电影文本获得了超越性的力量。那么,为何讲过无数遍的父女情,依然打动人呢?在《一秒钟》当中,这种动人之处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张九声如何突破规则与外部的重重束缚去接近女儿的形象。这背后的冲突实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公”与“私”的界限与分寸该如何把握?为什么个体的欲望与情感值得尊重、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撰文 | 重木
01
个体与外部环境的矛盾,
成为《一秒钟》的冲突内核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否暗示了某种宿命论般的无奈:即作为渺小的个体在这浩浩荡荡的洪流之中,往往无足轻重,恍如一滴水。
然而也正是在这里,我们遭遇了《一秒钟》中的矛盾。对于他人不起眼的一段故事,漫长电影中的“一秒钟”,对张九声这个从劳改营里逃出来的男人而言,却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对个体而言,他们所能感受和遭遇的往往就是全部,全部洪流的浩浩荡荡。
当张艺谋导演深情地追溯拍摄这个故事的原因时,提到了自己的早年经历,尤其是其中对电影的热爱和着迷。或许因此才会出现“一秒钟”这一象征和隐喻。作为组成一部电影的基本时间单位,是这些无数的一秒钟建构起了一部恢弘的电影。一秒钟与整部电影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象征着无数的个体与他们所参与、建设和创造的历史的关系。

《一秒钟》电影剧照。
在电影中,作为“一秒钟”的张九声女儿的影像既被强调又被忽略。一方面,这“一秒钟”是组成电影中重要新闻播报的内容,传递着当时整个环境的动向与潮流,如果没有这“一秒钟”,也就难以由此建构出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一秒钟”又遭到忽略,它(她)只不过是这支宣传短片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颗螺丝钉,被融入整体之中而不会受到真实的关注,而是被创造和需要的符号。
然而,张九声的出现则彻底破坏了这一潜藏的规则,导致那原本面目模糊的“一秒钟”中的女孩重新获得了作为个体的意义。产生这一颠覆的原因,则来源于由血缘这种自然因素所构成的亲情关系。
这一关于个体的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张艺谋电影中颇为出彩和矛盾的部分。从《活着》到《我的父亲母亲》,以及这个世纪中的《归来》,甚至《影》都流露出这一主题。张艺谋对这一问题念兹在兹,反反复复地回归和讨论中也流露出他所秉持的——以及几乎是整个第五代导演所关注的——人文主义关怀。
在《一秒钟》中,张艺谋通过在镜头下对一望无际且风声呼呼的高原粗野且恶劣的环境反反复复地展现,为观众营造出了一种令人紧张且萧瑟的气氛。汉娜 ·阿伦特使用“荒漠”来形容无世界性 (worldlessness)的状态,即一种人丧失了与他者一起共享世界的能力的状况。而张九声与刘闺女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个或许可以被看作是隐喻的漫天黄沙之中。

《英雄儿女》电影剧照。
当电影中出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火爆的《英雄儿女》电影时,我们其实被同时置于两种不同的叙事和观念逻辑之中:即在面对更高的、更宏观的理想要求时,个体可以如何选择。将《英雄儿女》与《一秒钟》相比,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差异,在《英雄儿女》中,王文清早早就发现王芳是自己十八年前无奈丢弃的女儿,但为了革命,他并未与女儿相认。而在《一秒钟》中,张九声为了能够看一眼自己的女儿,拼尽全力,甚至不惜威胁要杀人。
在这两种不同的逻辑背后潜藏着现代性中最为焦灼的矛盾,即对于个体的解放与自由,到底应该通过何种方式?
02
“私”与“公”的观念流变
对现代西方而言,“个体”从文艺复兴开始出现,之后在启蒙运动中成为一切研究的基础,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文学或经济、社会等。从中世纪关注神的目光转向尘世中生活的人。当人挣脱神的束缚而开始独立自主地立足于世时,启蒙哲学家们在人身上所发现的理性能力,便成为指导和帮助个体生活、思考和创造的最有力武器。“我思故我在”成为现代个体最核心的特质。
对中世纪神学的去魅带来的信心,让人们坚信利用理性便能够设计和建造出尘世间的天堂。曾经被圣奥古斯丁严格分别的“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在启蒙运动后的人类理性中渐渐被忽略;而伴随着科学技术等科技理性的发展,由工业革命所掀起的社会巨变,让人类对创造出一个对个体而言天堂般社会和世界的可能坚信不疑。
如何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对此回答出现的分歧也便成为现代世界革命中最典型的两条路:一条强调以个体的基本权益为主,通过社会契约建构国家与社会,保障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另一条路则是强调某种整体性方案,即只有通过对社会的全体改造,才能真正的解放个体与保障他们的自由与权利。

《一秒钟》电影剧照。
张艺谋与第五代导演遭遇的历史便是在第二条路的逻辑下所产生的,即为了创造出一个公平、自由、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必须彻底扫灭所有陈旧之物,在其废墟上重构新城和新的世界。也正是在这一典型的启蒙逻辑下,无论是《归来》中的陆焉识还是《一秒钟》中的张九声、刘闺女,都被要求为了这个更加崇高与伟大的未来和梦想放弃自身的“一己私欲”,参与到这一洪流的推动之中。
而《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王芳和政委也都确实积极且热情地参与其中,最终王文清与王芳的家庭悲剧在更高的理想面前被不痛不痒地化解。但这一逻辑在《一秒钟》中遭遇了危机与阻碍,从而才会由此揭露出风声呼呼的命运中的一些阴影,或是那些被遮蔽与不能被看见和知道的个体的遭遇与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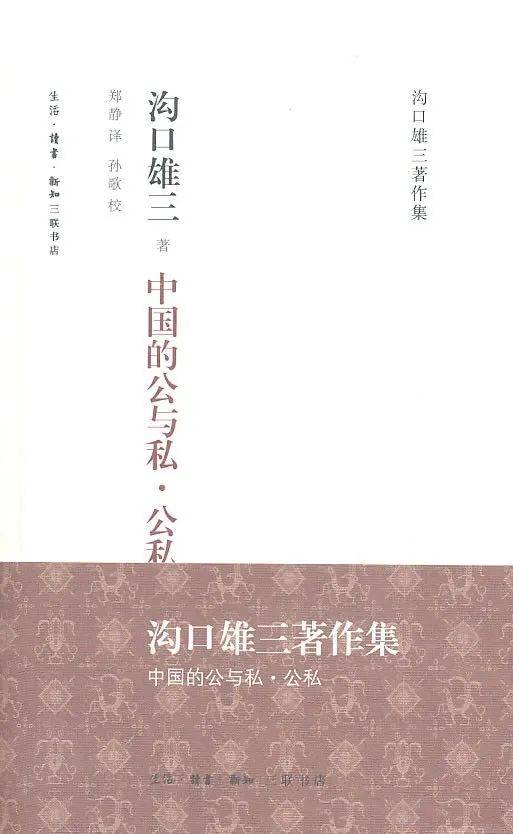
《中国的公与私 ·公私》,作者: [日] 沟口雄三,译者: 郑静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2月
在沟口雄三的《中国的公与私 ·公私》一书中,作者指出传统中国的“公私”观念与西方和日本都不相同,但它对近代中国在此相关概念中的影响却依旧十分强大。作为一种“由私的连带集结而成的公”,一方面因其具有协调能力而呈现出包容性,被理解为“公平、公正”;但另一方面,当它被视为“公平、公正”的标准时,作为其理论对立面的“私”便会遭到贬斥,无论是其道德还是政治中都由此渗入消极内涵。而《一秒钟》的故事却以典型的为私成了主流叙事之外的异类,从而遭到打击。
张艺谋选择以“父-女”关系来展现这一“私情”所具有的双面力量。为了看女儿一眼,作为父亲的张九声不惜破坏来自“公”的要求和命令,从而直接造成对后者权威的挑战和威胁。家庭作为传统中国政治与日常伦理生活中最基本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的便是“私情”,虽然我们也知道“公、私”观念最开始便产生自家族,即家族为公,组成家族的各方为私。为了家族之公,也必须压制各方之私。
但伴随着现代传统家庭在晚清之后的衰败,以及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家庭作为“私”便开始与国家或社会之“公”进行分离,甚至区隔。而组成近代核心家庭的生物性血缘关系也成为某种“私”的初始状态,因此当面对的是女儿、是弟弟或自己的儿子时,张九声、刘闺女和范电影才都会毫不三思地越过各种“公”的规章制度和禁令,保护对方。
03
与命运的冲突中,
个体如何摆脱无助与无奈?
正是在这样的亲情故事中,张艺谋似乎相信那些被看作“私”的东西其实更像是某种人性的自然情感流露。而在这样的“自然”中,外部机器所塑造和想象的未来才变得更加非人性化,而出现了康德曾经所担心的局面:即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工具。当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后开始反思到底是什么给现代欧洲造成如此大的灾难时,他们发现了工具理性这一幽暗之物所造成的理性与技术的疯癫。
工具理性在本质上强调实用与目的,从而与现代性革命中的整体方案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即被设定的目标需要机器运作般、条缕清晰地实施,而任何其他参与者、环境(“人定胜天”)和条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都必然为了服务这一目的而被要求牺牲其特性,成为“历史必然性”这部恢弘的电影中的一分一秒。在由工具理性所设计的历史和进程中,个体被以为公、为了更崇高未来的理由要求他们放弃私欲私情、创造性和能动性,积极成为组成集体的万千无名者。
在《一秒钟》的新闻播报中,张九声的女儿以及无数像她一样的年轻人,便在这样的时代呼声中奉献自我,就如当初的第五代导演一般。只不过后者稍微幸运些,活到了“时代变了”,但张九声的女儿却在这样的洪流中被淹没,仅在新闻播报中留下惨淡的一秒钟形象。

《一秒钟》电影剧照。
这样的遭遇也不仅仅只发生在女孩身上。当范电影因被张九声威胁而不得不给他放电影,在聊天中得知对方子女的不幸而获得短暂共鸣,以及其后他偷偷地让保安科来抓人,到最后他又剪下张九声女儿那一秒钟的镜头底片送给他……范电影身上体现出的才是真实且生动的人性——既不是天使、也非魔鬼,只不过是在各种境况下不得不或是无奈而造成的诸多形态。就好似张艺谋在《活着》中所展现出的那个纨绔子弟富贵的一生,在颠簸诡谲变换的时代中苟且偷生,获得些暂时的快乐和轻松。
但无论是张九声及其女儿的悲剧,还是刘闺女的不幸,甚至是范电影儿子的意外,都本不该如此。
在气势汹汹的新闻播报中,她的女儿只有“一秒钟”的镜头;而在历史和命运的潮流中,他们似乎也就仅仅如“一秒钟”般倏忽而过,且没有像范电影那样熟练的放映师能再通过剪辑来反复地循环这一秒。这似乎就是最后的关于个体的悲剧,即作为创造者本身最终却转瞬即逝且往往默默无名地像电影最后那截电影底片般,被黄沙吞没,再不可见。

《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加]查尔斯·泰勒著,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然而,张艺谋企图对抗的似乎正是个体在之后的时代叙事中再次消失的不幸。如果我们从另一层面看张九声和刘闺女的行为,或许同样能发现,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依旧坚持着自己认为是对的、需要去做的事情——尽管导致这些事情的原因是超出他们所能掌控的——从而在宏大叙事中书写着与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叙述。
在查尔斯 ·泰勒《现代性的隐忧》中,他把这一行为称作自决的自由 (Self-determining freedom),即当我们决定某样东西与我有关,而不是为外部影响所决定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张九声与刘闺女在亲情下所做的选择与决定,也便暗示着他们是自由的,即使在封闭且铺天盖地的时代之中,个体的“一秒钟”依旧能成为决定性的时刻,而超越外部的束缚。张艺谋也不正是在利用电影重新展现和讲述这些无数的“一秒钟”吗?
或许正如如汉娜 ·阿伦特在《政治的应许》最后所说,“正是因为我们在荒漠的状态下感到痛苦,我们才仍然是人、才仍然完整无缺。危险的是我们变成真正的荒漠居民,在荒漠中觉得像待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在《一秒钟》的荒漠里,无论是张九声、刘闺女还是范电影,他们都在遭遇着痛苦和不幸,也正由此才让他们饱有了生命的激情,而也只有如此——阿伦特说——“我们才相信他能够在自己身上唤起来自行动根基处的勇气,用于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只有行动的个体,才能改变荒漠,使其成为一个可供人与人进行连接、交流和一起行动的世界,也只有如此才能共同改变我们作为“一秒钟”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助与无奈。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撰文:重木;编辑:走走;校对:王心。题图素材来自电影《一秒钟》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
延伸阅读
我们对“做自己”三个字,有着怎样的误解?
- 无相关信息












